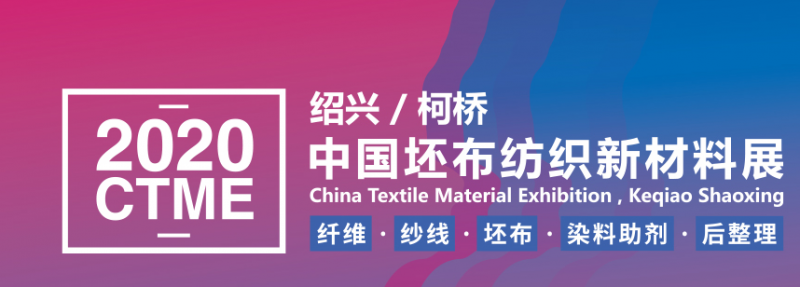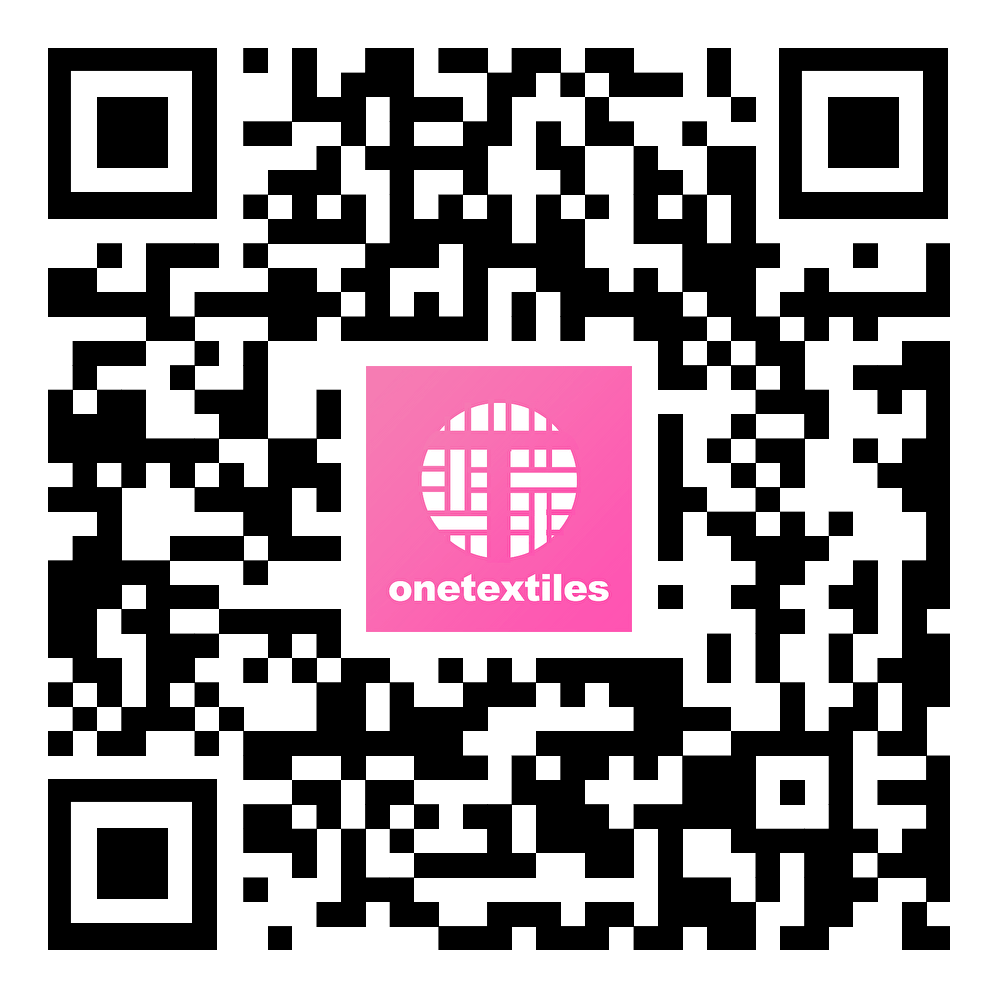服裝業“庫存”不是消費不旺的禍 滞後産銷機制是基礎
但對庫存市場來說,2012年是最好的年景。單單是42家服裝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存貨就達到483億元之巨。可以說,以廣州石井鎮庫存幫為主體的庫存市場迎來貨源最充沛的年份。
在中國的服裝集鎮中,廣州白雲機場附近那個叫石井的地方可能是最不知名的。現在,大多數的服裝企業需要他們,而很多普通消費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買的衣服裡有多少會來自那個甚至幾元錢就能收購一件羽絨服或者西裝的地方。
市場低迷,消費不旺并不是服裝行業整體沉淪的唯一解釋。近年來,在嚴重滞後的産銷機制的基礎上,品牌商那種無節制擴張欲和對暴利的無限向往,不斷地拉大理想和現實的距離,現在,終于,他們掉進了自己挖下的陷阱。
夏華相對一批2010年前生産的美邦正品很有興趣,但價格沒談攏,美邦倉管人員的出價是吊牌價的0.7折,而他的心理價位是0.5折。
在上海東南郊康橋路一帶的工業區裡,美特斯邦威(下稱美邦)是知名度最高的公司。與其他公司門前冷冷清清的境況不同,美邦總部的大門外總是車水馬龍,尤其是在周末。對很多上海市民來說,美邦的康橋南路800号是購物的好地方。
那裡的環境很好。一個橫跨馬路的偌大園區,幹淨整潔,聽不見機器的聲音—事實上,這裡是一個擁有龐大倉庫群的物流園區;對實行輕資産模式的美邦來說,這個倉庫區是300多家代工廠和4000多家門店之間的中轉站。
園區的綠化可能是國内最有特色的,美邦在庫門前的十多畝空地裡種下的不是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常綠灌木,而是郁郁蔥蔥的蘿蔔、白菜和花菜。在冬雨中,它們伴着地廣播裡的古琴聲生長。
美邦總部北側大門裡絡繹不絕的人流,并不是沖着長勢喜人的蔬菜去的,而是湧向菜地旁的特賣倉庫。園區内的指示牌上顯示,在靠北牆的倉庫内,有10多個品類上千個款式的服裝正在以2-3折的價格特賣,從5元的腰帶、帽襪到150元的大衣、皮衣,低價是美邦倉庫的魅力之源。即便是一些今年的新款,也在以3-5折出售。
“美邦的倉庫好大,每個倉庫裡有半徑兩米的大風扇,有十幾台可以升降的大叉車。”湖南人夏華相向記者這樣描述他所看到的壯觀景象,“他們有750萬件庫存,我的天!”對進入美邦特賣的倉庫的淘衣客來說,這樣的景象在他們的視線之外。美邦的倉庫群并不是哪個角落都可以讓外人自由出入,特賣區限定在20多個大型展廳裡,從這些标示某某品類訂貨廳的門牌上可以看出,這些展廳原本是供美邦代理商、經銷商訂貨之用的。
夏華相不是普通的顧客,他是專門收庫存的人,雅稱“庫存專家”。就在記者造訪美邦倉庫的幾天前,夏華相經人介紹,和美邦做了一單生意,以平均每件7元的價格買走了7萬件衣服,“從T恤衫到棉衣都有”。
之所以能夠以如此不可思議的低價買走,夏華相解釋說,這些服裝多少有些瑕疵,“但在我們那裡都還能賣。”夏華相原本對一批美邦正品的存貨也很有興趣,那批東西是2010年以前生産的。但在當天,雙方在價格上談不攏,美邦倉管人員的出價是吊牌價的0.7折,而夏的心理價位是0.5折。
對在廣州做了十多年庫存生意的夏華相來說,2012年差不多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年景。
單單是上市公司這些行業排頭兵就提供了極其充足的庫存貨源。按上市公司年中報,2012年上半年,國内42家公司的存貨總量高達數百億元,其中美邦服飾、森馬服飾以及李甯位列三甲,存貨量分别為17.53億元、14.73億元以及11.38億元。42家公司中,存貨量低于1億元的隻有4家。
随便哪一家的庫存貨全部拿出來,夏華相都消化不了。“我們收庫存,幾百萬一單的占多數。他們會一批批放出來,我們也會一批批收。”另外,關鍵的問題是“價錢要合适。”
“我們一般都是和管倉庫的人打交道。”夏華相不認識美邦的老闆周成建,也不知道周成建因為庫存問題曾經何其震怒。坊間傳說,周成建在今年初的一次内部會議上,大罵高管下屬們“三蛋一不”(混蛋、王八蛋、瞎扯淡、不作為)。
按美邦報表,公司上市後第一年(2009年)底的庫存為9億,而到2011年暴漲至25億。按申銀萬國的報告,25億存貨中,2011年春夏款及更早的庫存占了15億,占美邦淨資産(32億)的近一半。對夏華相來說,美邦五六億的2010年秋冬款及更早的款是他出手的對象。
對品牌公司來說,“吊牌價”在某種意義上是品牌尊嚴與榮譽所在,在美邦的倉庫店裡可以看到,哪些以幾十上百元出售的風衣、大衣吊牌價往往在千元以上,這個價位雖然在服裝行業中不算高,但其中起碼也包含了美邦研發能力、管理以及專賣店裡的服務。随便流失一項内涵,都意味着品牌的貶值。
比如,在美邦的工廠店裡,已經看不到專賣店裡店員們那種熱情的繁文缛節,記者走進工廠店的當口,一個工作人員對一個正在試穿大衣的顧客生氣地說:“跟你說過多少次了,這裡的衣服不能試穿!”
夏華相也并非不認同品牌的價值,“現在我們收庫存,基本上都要收名牌的。”隻不過,品牌永恒,品牌貨卻不是,“他們不能拖太久,服裝這個東西,兩年以上的舊貨是沒人要的。”
這裡是中國的服裝尾貨天堂。這是一個隐秘的生意。整個石井100多億的年營業額,對應的是正常渠道幾千億的銷售額。
記者第一次見到夏華相是在廣州白雲區石井鎮的慶豐服裝城。在服裝城的一個顯要位置,他經營着相連的五個檔口。在那裡可以看到許多英雄末路、被打回紡織物原形的國内外名牌:成包堆放的似新似舊的名牌充斥着檔口的一二樓,沙發上、茶幾和辦公桌之間的空隙也堆滿了名牌,進店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踩到它們。
那天下午,夏華相把幾個貨架的報喜鳥西裝樣品擺到檔口外的通道裡。這批吊牌價上千或幾千元、産于2009年的西裝是他兩三個月前的戰利品,總量有幾萬件之多,單價僅幾十元錢。為了維護形象,報喜鳥公司在賣出時把領子上的标簽剪掉了。
夏華相站在門外,極力向一撥女性客戶推薦一批新款的女款羽絨服。從客戶們的反應來看,這些服裝的牌子似乎頗為知名,夏華相開價是均價60元一件。此外,他還推薦了他剛從海瀾之家總部拉回來的毛衣,以及吊牌價在4000-5000元的“公牛”牛仔褲。如果你知道花100多元就可以在這裡買一條“公牛”牛仔,美邦倉管員0.7折的出價顯然有點太自負了—美邦隻是夏華相考察過的成百上千家貨源公司之一。
“這裡是中國的服裝尾貨天堂,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夏華相的朋友、福建人陳付陽對記者說。石井鎮的确有那麼一點國際化的氣息,在鎮上廣大、慶豐、錦東等幾個服裝城裡,不時會看到扛着大包衣服或者正在檔口看貨的黑人或者中東人。有個沙特大戶是石井的常客,“他每年來四五趟,帶着翻譯,一個檔口一個檔口目不轉睛地看,一般一個禮拜就會搞定一單。”陳付陽說,這個沙特人一年從石井進貨三四個億,曾經一次拿了8000多萬元的貨。
并不是每個沙特人都是靠石油緻富的,沙特人收走的恰恰是均價10元錢以内的超級便宜貨,“整個中東地區都沒什麼服裝企業,他應該是賣到中東的其他國家去了。”
“不管什麼牌子,是T恤還是羽絨服,庫存拖到不得不出的時候,收購均價也就幾塊錢一件。在我們這裡,不管是我們收進還是賣出,都是遠低于生産成本價。”陳付陽說,“服裝又不是金子,能保值。那些服裝廠商總以為,100塊錢成本的衣服,為什麼要三五十塊賣給我們呢?他們舍不得。
于是就一直壓着,可這東西越壓越不值錢。比如2008、2009年的貨,已經不是價錢的問題了,就是幾塊錢給我們也賣不出去。現在即使在偏遠地區,大衆的需求也是要漂亮,要款式好。”對那些庫存積壓如山的上市公司來說,留給他們的時間并不多。
按服裝行業的成本結構,大中型服裝企業的生産成本約到吊牌價的1.8至2.3折。在庫存市場上,需要的不是對價值的尊重,而是對愛便宜心理的尊重。
不管服裝廠商多麼看不起這上不了台面的庫存生意,他們也不得不正視自己的處境。庫存生意始終與中國服裝行業擴張過程如影随形。1998年,當17歲的陳付陽揣着2000元錢,離開福建龍岩永福鎮那個花農家庭,跑來投奔哥哥陳付峰的時候,石井聚集着一個龐大的庫存商幫。從最早的廣大服裝城開始,如今的石井已經有四五家大型服裝城,上萬個商鋪。
全鎮的尾貨生意,按陳付陽的估計每年有100多億的交易規模。盡管商戶聚集度極高,石井的店租仍然是十分便宜,一間20多平米的鋪子,月租隻要3000元,按夏華相的說法,石井的尾貨商鋪不用交稅,不用交管理費,“在廣東這種地方,這麼小的生意他們(政府)看不上。”
沒有廣告,絕大多數的石井商戶時至今日也不在網上發布信息。為數幾萬人的尾貨群體中,即便是陳氏兄弟這樣的大戶,也是服裝業内毫無知名度的老闆—他們差不多是一個隐秘的群體,隻有圈子裡的人才會彼此認識。
“有時候住進一個賓館,裡面的住客我可能有幾十個都認識。我最近在青島機場等飛機時也碰到好多個熟人。你想,幾萬人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出出入入,肯定都會碰到的啦。”
似乎在國内的任何地方,來自福建的行商者都很容易聚集成群。按陳付陽的估算,在石井的尾貨市場,福建人占了1/4。隻不過,尾貨并不是某個地域商幫壟斷的生意,“潮汕人、四川人也都有幾千。”
福建商人強烈的擴張欲成就了年僅33歲的陳付陽。在石井,他不單經營着一二十個檔口,還和石井的福建商會會長投資合建了“盟佳童裝大世界”的物業。在這個童裝世界裡,每年銷售童裝5個億,占到石井童裝類市場的一半。“那些起步更早的人,現在基本上都不再親自跑尾貨,而是把檔口交給帶出來的人去經營,自己搞房地産或者其他項目去了。”
陳付陽說,在石井的庫存市場,投入一個多億現金去做的人算是大鳄。這個數字,乍看起來和那些大型服裝上市公司相比不算什麼,但在庫存市場,資金的周轉效率高得多。
在服裝産銷企業裡,一年最多做四季服裝,投資周轉四次,而在石井周轉是不限次數的。“一個億是什麼概念?按服裝産銷企業的正價至少相當于5億。而且,我們今天收幾百萬,明天收幾百萬,資金一直在滾動,5億這個數字還得翻好多番。”
坐在盟佳童裝大世界“海绮隆服飾”的店堂裡,陳付陽指着密密麻麻的貨架對記者說:“這些樣品今天還挂在這裡,可能明天就整批賣完了。”陳付陽一共操作了100多個牌子的尾貨,樣品多到店堂裡根本都挂不下。“每個牌子的貨,我們都是以幾萬件為單位。要知道,一年産銷幾百萬件服裝,在中國已經是超大集團公司了。”
至于整個石井這100多億的年營業額,則是一個更驚人的數字,按尾貨的價格杠杆,對應它的是正常渠道裡幾千億的銷售額。
服裝企業的高庫存是問題多年累積的總爆發。一個服裝企業的倒閉,往往是庫存幫大有作為之時。
在石井,我們能看到一種最講江湖規則的生意。“你如果能找到一單貨,讓我去收,能賺10萬塊錢的話,我分你5萬。資金利息、倉庫租金和其他費用都不用管。”很多年以來,石井的店主們都是和找貨人如此分賬,雙方沒有合同,依據的是行當裡自發形成的慣例。陳付陽說,在石井的童裝圈子裡,這種靠四處看貨,和檔口老闆們共赢的人有幾百個。
他很依賴這個群體,“我每天要接五六十個他們打來的電話,在五六十單生意裡,我會選擇性地看上幾單,然後挑兩三單貨拉回來。”
他自己就是這麼走過來的。17歲的時候口袋裡揣着的那2000元錢,“在外面坐公交車、買瓶水,吃頓午飯,一天的生活成本10塊錢。手裡的錢是根本不夠打貨的。”但就是靠今天收一匹布,明天收一包衣服地攢錢,七八年後他當上了老闆。
跑出去拉單并不容易,“人要熟,貨要看得準,要會砍價;現在盡管貨源充裕,但競争也很激烈。你要知道,哪個行當裡都是老虎比豬多。”早些年,陳付陽出門看貨,往往一去就是一兩個月。
在杭州開過童裝廠的胡海東和陳付陽打過幾年交道,很欣賞陳的行事風格,“他過來收貨的時候,我們并不讓他進到倉庫裡去,隻是把樣品拿出來,然後告訴他有多少件。他看上了,就把定金放下,我們去裝箱,他第二天就過來把貨拉走了。”有一些謹慎的尾貨老闆,往往臨時雇幾個人去清點件,陳付陽比他們要痛快得多。
2010年,胡海東幾萬件庫存被陳付旺一次性清得幹幹淨淨。“如果碰到大倉庫,庫存數量太大,他就會聯合圈子裡的幾個人一起來收。”胡海東說,這個群體的存在很有必要,庫存堆在那裡已經是廢品,多少能回收一些資金,總比借民間高利貸來補充流動資金要好,尤其是近年,各地高利貸的行情都到三分以上了。
“一單幾萬件的貨,少個幾百件,或者摻了一些次品,對我們來說可以忽略不計。我們隻是按各個品類的比例來給一個均價。”陳付陽說現在的庫存貨源實在太多了,“現在全中國生産的童裝包括庫存貨,國内的孩子十年也穿不完。”這話可能有些誇張,但也接近事實。
正如胡海東所指出的,如今服裝企業的高庫存是問題多年累積的總爆發。“你想,很多企業的倉庫裡還堆着三四年前的東西呢。年景好的時候,有一些庫存可能沒什麼,可現在很多企業都嘩嘩地關店,庫存能把企業累死。
“除了童裝,2008年前後上市的那批體育用品企業如今都是庫存大戶,這些上市公司的年中報顯示,包括李甯、匹克、鴻星爾克等在内的幾家公司已經關掉了1000多家店鋪。渠道收窄,對于庫存清理更是雪上加霜。
胡海東曾經在福建和東莞的成人裝和童裝企業擔任高管,對服裝産銷的弊端頗有發言權,“國内企業的産銷周期太長。企業做生産計劃,往往是一年前就開始打版,下單,可現在的服裝時尚感越來越強,誰能知道一年後市場到底流行什麼?”而對幾年前那些急于上市的公司來說,往往是在上市前沖量,貸着款去擴充渠道,“這些都造成了一種需求的假象。”
内銷公司如此,外貿的萎靡對今日中國的庫存規模也貢獻甚大。“現在沿海的海關,都堆着相當多的垃圾貨;公司倒了,東西都滞留在海關。一單就是幾十萬件,這樣的生意現在多得很。”陳付旺說。
盡管一些知名公司對庫存幫往往表現倨傲,但到了一定時候,他們也會有求于這些江湖上的及時雨。幾年前的一個晚上,陳付旺就接到一個東莞打來的電話,說是一個老闆急需2000萬元現金。陳付旺連夜聯系人把錢湊齊了去拉貨,就在最近,陳付旺的朋友還做了一個1700萬元的大單。
不要低估庫存幫的能力,伴随着服裝業的多年擴張,庫存幫也在擴張,“以前我們湊2000萬,要很多個檔口,一家幾十萬地湊,現在隻要兩家就能拿出來。”陳付旺說,這個行當全是現金交易,不賒不欠,再沒有比這簡單直接的生意了。
一個服裝企業的倒閉,往往是庫存幫大有作為之時。對那些工人排在廠門外等着要工資的工廠而言,庫存幫的現身意義重大,“工廠倒閉往往是工資拖着,廠房租金拖着,債主的錢欠着。工廠的人也好,政府的人也好,隻要有人和我們談價格,我們就去拉,一手錢一手貨。”
“暴利心态導緻了整個産業鍊的畸形。比如,這件衣服100塊錢成本賣1200,于是很多人跟着這麼做。其實服裝本身是個低平台的産業。”
“隻要人類還穿衣服,還在生産服裝,就不可能沒有庫存。”百川一代服飾的業務員周吉祥,差不多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向記者解釋庫存産生的原因。這位87年生的年輕人來自長沙,和他那位湖南同鄉夏華相一樣,在幾百上千家企業看過尾貨。
“企業處理庫存,首先是在自己的店裡打折賣,賣不完就甩給我們或者捐贈給邊遠地區,再處理不完就銷毀。”周吉祥說,歐洲的奢侈品品牌也是這麼幹的。
我們在中學的教科書上,讀到了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把以百萬加侖計的牛奶倒進陰溝的内容。這是否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值得商榷—因為牛奶可能過期了。至于服裝,其實是會過期的,“在倉庫放了超過兩年的服裝,多少會發黴,穿上去線都可能崩掉。”周吉祥說。
我們至今沒有獲得哪家企業公開在銷毀服裝的消息,勤儉起家的中國服裝商人的道德水準也大概高于那種過剩資本主義時代的美國商人。不管怎樣,對中國服裝業來說,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在石井錦東國際服裝城,記者見到了周吉祥的老闆、百川一代服飾的總經理廖亮中。據陳付陽介紹,在成人裝領域,廖亮中是石井的大戶。在等待廖亮中的那天下午,記者看到了服裝城裡穿梭的“百川一代客戶服務車”,以及很多家“百川系”服裝店,愈加相信陳付旺關于“廖是服裝城的大股東”的說法。當天,百川的一個檔口正在以一折到一點五折的價格賣“國際品牌”DEVIDERO和BULL。按廖亮中的規劃,錦東服裝城要做成一家奧特萊斯,而不僅僅是賣邋邋遢遢尾貨的地方。
42歲的廖亮中來自廣東梅州,服裝打版師出身,1992年在廣州開過服裝廠,随後在廣州的黃埔、東山口開過很多家專門賣庫存貨的零售店。2000年以後,他也加入了石井的庫存幫。
對于服裝的高庫存,他另有一番見解:“中國的服裝企業在曆史上有暴利,吸引了很多人去追逐。暴利心态導緻了整個産業鍊的畸形。比如,這件衣服100元成本他賣1200元,還賣成了。于是很多人就跟着這麼做,其實服裝本身是個低平台的産業。”
為了賣高價,服裝企業都紛紛往高端商場擠,但高端商場見誰都要砍一刀,“商場扣點28%。就算是一線品牌,都要走很多關系。比如,你在廣東要進一線商場,就必須找對幾個人,給個50萬元、100萬元才能進去。這些花銷都攤到成本上去了,價格自然就扭曲了。”
即使是街店,前幾年租金也是異乎尋常的高,“東山口、黃浦一帶的商業街,鋪面租金都是天價。一個月下來,幾間店鋪就賺萬把塊錢,可如果我不幹了,把店轉租給别人,可以收到八九萬元租金。
“尤其在2002年以後,運動品牌迅速崛起時,全國各地商業街的店租更是扶搖直上。運動品牌對這筆成本早就難堪重負,沒上市的公司支撐不住,即使上市了的公司,現在也不行了。因為經濟低迷,消費規模也小了很多。
高昂的渠道成本加上消費的低迷,直接導緻了服裝行業的快速下滑,“據我所知,一二線品牌的動銷率不到50%,甚至有些人的動銷率不到30%。這樣一來,市場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想做一個奧特萊斯,走量的同時追求合理的利潤。”這個設想正在變成現實,現在廖亮中的一處樓上樓下400平米的店鋪,一天能賣兩三萬塊錢,好的時候四五萬塊錢,而店租一個月隻有萬把塊錢。“這好過花5萬塊錢在繁華地段去租一個店。我的主業是批發,但現在零售都可以支撐我的開銷。”此外,百川一代和其他服裝企業不同的是,流程簡單,沒有那麼多附加環節的開支。
廖亮中認為,服裝行業的暴利時代應該終結。“那些上市公司曾經是高利潤啊。我們的利潤率隻有30%,而他們曾經有300%的利潤。”今天的巨量庫存不過是為當年的暴利付出的代價。
要消化服裝業的巨量庫存,靠專賣店裡慢悠悠地打折銷售,或者工廠店裡的特賣顯然是不夠的,而寄希望于電商則更不現實,“庫存貨往往款式多而單款量少,而且,我們要求很高的周轉率,把一件件不值多少錢的東西,分類整理、拍照,然後雇很多人挂到網上去賣,是不劃算的。”
在很大程度上,石井鎮是服裝庫存最後的去向。然而,即使到了石井,庫存也還拖着一個長長的尾巴,像廖亮中、陳付陽、夏華相他們,是庫存市場的第一個層級,接下還有找他們幾千幾萬、幾十萬地打貨的全國各地庫存分銷商。
誰也沒法保證石井庫存能完全被消化,“我們現在非常謹慎,因為我們也有庫存。今年上半年,我收了一百多萬件衣服,到現在還有15%沒賣掉,這對我們來說是很不正常的。”廖亮中說。
特别提示:本信息來源于中華紡織網。本文僅供參考閱讀。
如涉及版權侵權問題請聯系我們,我們将及時删除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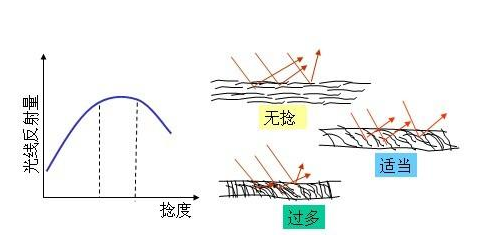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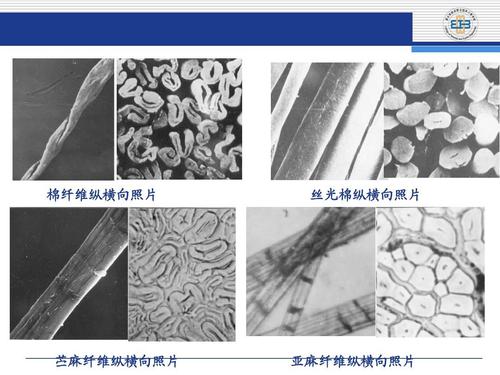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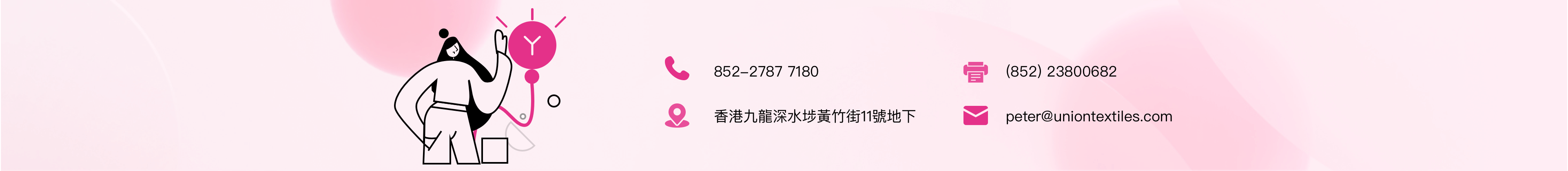



 微信小程式
微信小程式